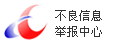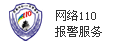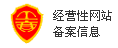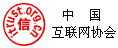填表的内容同样让人费神费力。
比如每年搞大项目的预算,每一部分比例要符合基金的要求,仪器设备费、人工费、实验材料、测试费、国际交流费,参加几次国际会议都要列出来,要去算,“一个上千万元的大课题,要算多久啊!”
龚教授说,很多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,也不知道怎么算,“因为最后要算一个符合申报规定的东西,但是肯定不是真的,谁能预料中间的变化呢”。
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对此深有同感。
他介绍,即使在人文学科,一个表格填四五天也很正常,“每栏要填三四千字,最后填下来一两万字,还要去查很多数据”。
在他看来,一些表格的设计很奇怪,比如为一个课题填表,需要分别填写两栏,本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和本课题的创新之处,每栏限3000字到4000字之内。
这让他感觉很荒谬,“创新之处不就是成果吗?”
作为申请者,王彬彬教授的经验是,每栏都要填满,表格交上去,别人都写了很多,你只写了一点点,评委就会觉得你态度不端正,要减掉很多分;与此同时,两栏里内容还不能完全一样,“一样的意思还得换一种说法,如果完全一样,评委也会觉得你态度有问题。”
“这样一来有个危险,本来正常的学术团队就演化为‘大佬+团伙’了。”作为973首席科学家的龚教授发出警示,“大师+团队”能做出很漂亮的科研成果,但是如果每个人每天都在干这些虚的活,没有时间研究重要的科学问题,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。这就演化成“大佬+团伙”,和江湖人的生活很像了,“他能赚到钱,但是他没有产品,无法为社会作贡献。”
“如果没有会,就是我的lucky day”
一位科学家自嘲,不是在开会,就是在开会的路上
“我几乎每天都有会。如果没有会,就是我的lucky day。”说起科研时间被侵占,北京一家研究院的王教授有道不尽的苦水。
王教授是中科院2004年的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,2005年初全职回国,太太和孩子都在国外,本想一心一意地在国内做科研,没想到常年会议缠身。
他介绍,每周填表量不在少数,同样让人烦心的还有会议。王教授每周上班时间大概要参加4个会议,有党政的会、学术的会、外事的会、后勤的会等等。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,他好不容易才推了北京市一个单位的评审会议。
周六周日,王教授还要去参加一些评审会,这是因为一些科研领导部门怕平时人难凑齐,把很多评审会都定在了周六周日。
所有这些会议,几乎没有一个小时内结束的,更多的情况是到外单位开会,一下就要花掉半天时间。
“不是在开会,就是在开会的路上。”王教授一脸苦笑地自嘲。而让他一直不适应的是,国内的会议往往根据领导的时间定,刚说完下午两点半开,马上就可以改到3点。
为了帮助自己所在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,王教授还需要接待大量的外宾,每周需要审阅至少一篇国外或者中国学术刊物的稿件。
由于北京堵车,王教授每天早晨5点半就得起床,堵车之前到学校,在学校食堂吃完早餐,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王教授说,真正属于自己的科研时间主要有两块,一个是中午,20分钟左右吃完饭,从来不休息,也不运动,省下来的1个半小时是学习、处理学问的时间段;下班之后大家堵车的时间,王教授到食堂匆匆吃完饭,又赶到办公室,9点钟左右才开车回家,“那是我做学问最好的时间,这个时候大家都累了,也就消停了”。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中国科学家,特别是知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成为突出问题。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证科学家5/6的工作时间。中科院甚至专门成立了时间办公室。
中科院吴国雄院士感觉现在已经到了比以前更严重的程度:到65岁退休,一半的时间都在开会,所以一个人科研的周期缩短了一半,对国家的损失很大,“现在是老院士开会,年轻人也开会,中年人也开会,会议扎堆儿。”
吴国雄院士被开不完的会议搞得很苦恼:不少会议是熟人组织的,不去会得罪人,去了浪费时间。有时候他干脆带着东西做自己的“作业”。
SARS疫情暴发时,各式各样的会都没了,他埋头做学问,3个月他与合作者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。但此后好长时间,都写不出好文章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