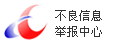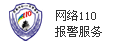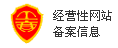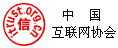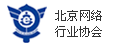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�
�Ͼ�һ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̡� �� 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ʩϸ��(���¼�ơ�ϸ��)��5��1����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ʱ�䡣��ϸ��ʮ�����涨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ý���Ϊ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ķ�����ʵʩ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ոչ�ȥ�ĵڶ�ʮ�ĸ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֮��ǿ�ҡ�Ϊ�ˣ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鷢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 ִ�����岻��ȷ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 5�µף��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“�˿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Űѹ˿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˿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Ӫ�߱�ʾ֪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̹˿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˭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Ӫ�߱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и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ľ�Ӫ��Ӧ��Ϊ��ֹ���̹涨��ִ�����塣����ʵ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Ӫ�߳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濼�ǣ�����ԸΪ��һ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˿͡���½�ֹ���̵���ع涨�ڲ������ưɵ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ֽ���ġ����ϲƾ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о�Ժ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з��ɿ���ھ�Ӫ�߳�����ֻ��Ȱ��˿����̡���Ϊ�ӷ����ӽǷ�������Ӫ�߲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壬��Ӫ�߲��ܶ�Υ�����ɹ涨�Ĺ˿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߲�ȡ�κ�ǿ���Դ�ʩ��
�����з���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䲼�IJ��Ź��£�ȫ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ó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塣����ʵ�У��ھƵꡢ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Ա��ʱ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Ƿ�ë��ǡ�“�ҹ���3�ڶ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̵ص��ֺܷ�ɢ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ɢ��Ҳ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ҡ�”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ѧԺԺ��Ѧ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��˭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Ȩ��ִ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辯�����ִ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첻��Ҫ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潶IJ���Ϊ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飬��Ҫ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飬һ������Ӫҵ�Գ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ģ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�ȷ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Ӫ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̶������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ʱ���룬ȷ����ֹ���̵Ĺ涨�õ���ʵ��
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ڹ㶫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Ư���ź�ζ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Ʊ�����̶���Ա���ʶ�˵��“ÿ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IJ�����20�ˣ��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ij˿����Ƕ���ԱҲֻ��̾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ҽԺ�ͳ�վ��Ϊ��Ӫҵ�Ե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Ŀ��̲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̴�ʩ����Щ�ط�Ҳ����ִ�У��йط���ר�ҳƣ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ʩ������˥����Ҫԭ��
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λ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IJ��Ź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ɲ㼶�ϵ͡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е�ʮ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涨��
����“��ϸ��δ��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涨��Ҳ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ϸ�Ĺ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й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ԵĹ����̲ݿ��Ƶ�ר�ŷ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漰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ȫ���Է��ɷ����У�֪ͨ�Ե���ʱ�Թ涨���ᳫ�ԵĹ涨�Ӷࡣ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“Ϊ��һ����չ�̲ݿ��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ƿ��̷��棬�ڽ��̷��澡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Ϊ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Υ���ɱ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ط�ʮ�ֱ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ҽ�Ʊ��ձ��ѻ���Ӧ��ߡ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ȶԾƼݵ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Ӵ��Υ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ݳ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ٴ���Υ����”Ѧ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Ŵ�ѧ������ɽҽԺ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ʱ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˶�û�С�����֮ǰ�ĺܳ�һ��ʱ���ÿ�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λһֱ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5��IJҵ���Ӫ����1996���22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ɴ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Ŀ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ʵ��”����ͳ�ƣ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00—400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”�IJ������ɡ�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ﲻ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ϡ�٣�ҽԺ���ܲ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ø�����”�й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ڿ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һ����ҽԺͳ�ﻮ�֣����ҶԽ������ィ������ת���ʽ�û��Ͷ�롣�Դ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Χ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̲�˰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ʽ����ڿ��̣��Ӿ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ȷ���֧�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